透过车窗望北京
发布时间:2022-02-25 文章来源:CSCSE 文图提供:CSCSE
[英国] 冯语旭 北京师范大学
今天早晨,嘤嘤成韵的鸟鸣声把我吵醒了。我半梦半醒地听着它们的表演禁不住微笑。不知为什么,随着时间的流逝,鸟鸣的声音越来越大。我觉得很奇怪,原本安静的晨歌突然变成又嘈杂又惊人的一团糟。我在漆黑的房间里睁开眼睛时,才发现那个声音不是鸟鸣而是我的闹钟。5点47分,起床喽!我住在一个离校园比较远的小区里,因此不得不坐公交车去上课,所以每天起床早得让我想哭。我透过公共汽车的窗户,看着酷热的夏天变成凉爽的秋天,分外短的秋天突然变成灰暗的冬天,悠悠的冬天慢慢地融入温暖的春天,最后看到春天飞驰而去又变成一个新的夏天。
住在一个校外小区而不是学校宿舍利远大于弊,因为我能亲身经历中国的小区文化。那不但能让我更清楚地理解中国人的想法,而且它给我很大的安全感,让我的生活又舒服又稳定。每天早晨我有个自己的程序:首先我坐拥挤的电梯下27楼,然后我去大楼下的小超市买早餐,一边用微信付款,一边很困地跟超市的阿姨打招呼,最后我直奔小区东门等候带我去学校的620路公交车。
620路的特点就是它很难预料。有时候我很容易就找到一个在二层的座位,如果那样,我就会打开窗户,享受微风拂过脸的感觉,让自己沐浴在温暖的朝晖中。虽然早晨半睡半醒时,没有什么比寂静更好,但是620路的乘客常常给我的生活带来许多有意思又热闹的交际互动。比如说,坐公共汽车时,如果我打开一本中文的书,这总会吸引别人的注意,他们会过来问我“学习中文多久了”“住在北京多久啦”“你是哪国人”之类的问题。我刚来到北京时之所以不习惯这样的交流,可能是因为在英国人们很少会跟陌生人交谈。因此,为了避免别人问问题,更是为了保持个人的空间,我在中国时每每会戴上耳机假装自己在听音乐。

有一天,当我站在闷热的8月某个早上的拥挤不堪的公共汽车上时,我碰到了两个很有意思的女士。因为那天乘客分外多,所以我不得不站在一层和二层之间的楼梯上。在我旁边有两位女士一直偷偷地看我。我们到了奥体东门站时,我向这两位女士的方向转了头看看在二层有没有空的座位。她们看见我的面孔时,一位女士对她的朋友说:“哇!他的眼睛很好看!”我知道她们以为我听不懂汉语,我心里暗暗得意,于是笑着对她们说:“谢谢。”
我们到了北土城站时,乘客突然减少了许多,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座位。在公共汽车二层的前面有一台小电视,在屏幕上出现了各式各样的新闻和节目:英国准备脱欧,两位明星嘱咐老百姓“不剩饭,不剩菜”,另一位女士教观众怎么烘蛋糕,一个穿汉服的卡通女孩儿给我们解释中国梦的思想内容。当小电视开始重播我已经看过的视频时,我转头望向下面的林荫大道,陷入了沉思之中,仔细想着我生活在中国的这一年会怎样。
我最初接触普通话是我在香港上高中的时候。所以初来乍到时,我还是用繁体字,说“这里”时也从不用“儿”这个很生疏的字。到了北太平桥南时,我麻利地站起来提前做好下车的准备。下车时,望着即将要进入的大学,我不由得浮想联翩。
将近一年的时间不知不觉地匆匆而去了,一切的一切都改变了:我听得懂甚至可以说精通的士司机的话语了。还有,我在中国跟陌生人交谈也没有什么问题了。我明白这样的行为,非但不是一个需要为此烦恼的事,反而不失为一个能理解中国人想法的好机会。随着时间的推移,我渐渐地把中国人的好奇心看作一个很积极热情的表现,也就是说,我适应了当地的风土人情。
不幸的是,现在我得告辞了啊,北京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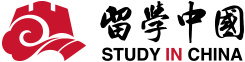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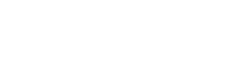

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35730号
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35730号